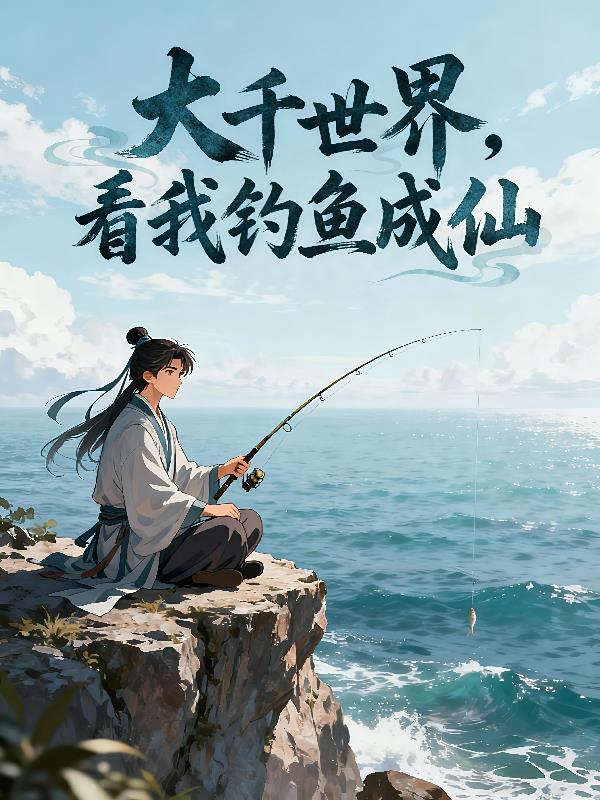天才一秒记住【小说中文网】地址:https://www.xiaoshuocn.net
北京外城的泥土路刚刚化冻,变得泥泞不堪。
锦衣卫指挥使衙门深处,陆铮换下一身令人敬畏的蟒袍,穿上了一件半旧青布直身,外罩寻常棉马褂,看上去像个家境尚可的账房先生或小商铺管事。
陆铮身后跟着两名同样便服的精悍男子,是他的贴身亲卫,沉默地保持着警戒距离。
“大人,今日想去何处?”亲卫百户低声问道,他叫陈默,跟了陆铮三年,脸上有一道淡淡的疤。
“随处走走,看看,听听。”陆铮的声音平静,目光却已投向衙门外那喧嚣而混乱的市井,“看看朝廷的法度,到底落在了何处。”
第一站是通惠河畔的漕运码头。空气中混杂着河水腥气、汗臭和货物霉变的味道。
力夫们赤着膊,喊着低沉的号子,脊背被沉重的麻袋压得弯曲,在湿滑的跳板上艰难挪步。
陆铮在一个冒着劣质烟丝的茶摊坐下,要了碗最便宜的粗茶。摊主是个独眼老头,手脚麻利,却沉默寡言。
旁边几个刚卸完货的力夫,瘫坐在条凳上,骂骂咧咧。
“日他娘的‘漕折’!说是为咱好,省得运粮苦!可活儿没见少,工钱倒他妈跌了!”
“王五哥,知足吧!南边好几个码头的兄弟都没饭吃了!听说上头老爷们把钱折了银,层层扒皮,到咱这就剩这点碎渣!”
“狗屁新政!换汤不换药!苦的还是咱卖命换饭的!”
陆铮端着粗陶碗,热气氤氲了他没什么表情的脸。
陈默站在他身后,手指无意识地按在腰间的短刃上。陆铮微微抬手,示意他放松。
《崇祯五年安民裕国疏》里的“漕粮折色”,在阁部大臣的奏章里是利国便民的好策,落到这泥泞的码头,却成了力夫们咒骂的由头。
减少的运输损耗和增加的国库银两,是以这些最底层劳动者的生计受损为代价的。政策的制定者,看到了宏观的数字,却看不见微观的苦难。
陆铮几人离开码头,步入外城集市。人流如织,叫卖声此起彼伏,看似繁华,细看却透着一股焦灼。物价高得惊人。
陆铮在一个粮摊前驻足,抓起一把米细看。
“客官,好眼力!新到的河南米,煮饭香着哩!”粮贩热情招呼。
“怎如此之贵?”陆铮问,语气平常。
粮贩脸一苦:“哎哟,我的爷!您是不知啊!河南那边道是顺了些,可一路上的税卡、漕衙的常例,一分没少!再加上今年天冷…就这价,咱也是赚个辛苦钱!”
陆铮又问了布匹、盐价,无一例外。河南清丈、整顿驿道带来的微弱流通改善,完全被固有的盘剥体系和层层加码吞噬殆尽。
百姓并未得实惠,反而要承受更高的生活成本。他心中那份由河南抄家清单带来的些许成就感,凉了下去。
沿着官道走出数里,一处破败的驿站映入眼帘。院墙倾颓,荒草齐腰。一个穿着破烂号衣的老卒,蜷缩在断墙下晒太阳,眼神浑浊,望着虚空。
陈默上前,递过去一块硬面饼。老卒愣了一下,一把抓过,狼吞虎咽。
“老丈,曾是驿卒?”陆铮走近,声音放缓。
“嗯…三十多年…”老卒噎住了,咳嗽着,“说裁就裁了…那点银子,够干啥?儿子…儿子跟人跑口外去了,没音信…等死喽…”他喃喃着,像是说给别人听,又像是自言自语。
陆铮沉默地看着他。裁驿充饷,省下的经费或许变成了兵部账册上的数字,或许变成了通州新军碗里的一块肉。
但眼前这个老卒,和他背后成千上万被裁撤、安置不善的驿卒,却被彻底抛弃,成了帝国改革的牺牲品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。他们的绝望,是李自成们最好的兵源。
心情沉重间,陆铮几人走到了京营家属聚居的区域。这里的房屋同样低矮简陋,但显得整齐些,也多了一丝烟火气。几个妇人正在井边浆洗衣物,聊着家常。
“当家的捎信回来,说营里晌银足着呢!这个月还能多捎回些!”
“曹将军是凶,可不贪咱穷军汉的钱!练是苦,可练好了是真本事!”
“盼着吧,盼着娃他爹立点功,咱家也能换个大点的窝…”
听着这些充满希望和期待的闲聊,陆铮冰封的脸上似乎有了一丝微不可察的松动。
张焘、曹文诏的严酷训练,锦衣卫对粮饷的严密监控,在这里转化为了最实际的效益——军心稳定,家属安心。
这是他今日之行,看到的唯一一点切实的、正向的改变。虽然范围很小,却如同寒夜中的一点微光。
回城路上,经过一座破败的土地庙。里面挤满了面黄肌瘦的流民,多是去岁北地灾荒南下的。
朝廷虽有“安民归业”的政令,但显然力不从心,只能设粥棚勉强维持,饿殍虽未遍地,但绝望的气息弥漫。
一个穿着洗得发白长衫的年轻书生(像极了杞县的张文远),正努力地教几个流民孩童认字,声音温和却无力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喜欢大明卫请大家收藏:(www.qidianxin.com)大明卫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。